第二章 浪子的“道”(2/9)
最终才有了侠客 子。
子。
我一直倾心于侠骨柔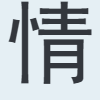 的金庸,他笔下的
的金庸,他笔下的 物虽漂浮在不知方位的虚空,可我总能亲切而默契地认同。虽是虚幻,却在一个
物虽漂浮在不知方位的虚空,可我总能亲切而默契地认同。虽是虚幻,却在一个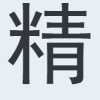 神层面上完整而永恒地突显了被潜抑的渴求,无奈和对无奈的失落在这儿寻求着各自的平衡。
神层面上完整而永恒地突显了被潜抑的渴求,无奈和对无奈的失落在这儿寻求着各自的平衡。
文明渐渐走进,现代 对蛮荒的遥远记忆已留存无几,却又久久不能割舍。
对蛮荒的遥远记忆已留存无几,却又久久不能割舍。
原来生命的核心本是莽苍苍的自然,所以 子并非一定要去
子并非一定要去 迹天涯,在
迹天涯,在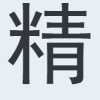 神世界的天涯海角营造
神世界的天涯海角营造 子的心境,或许更不容易被周遭同化。
子的心境,或许更不容易被周遭同化。
 子的心境便是要领略一种
子的心境便是要领略一种 层次的孤独,却又要温和、自在地活在繁华喧嚣间。遁
层次的孤独,却又要温和、自在地活在繁华喧嚣间。遁 空门的佛家子弟、云游四海的道士不是
空门的佛家子弟、云游四海的道士不是 子;厌弃红尘,消极避世的王维、陶渊明不是
子;厌弃红尘,消极避世的王维、陶渊明不是 子;以孤独作茧,躺在茧里作蛹,仅以一种寄托作为出气孔的八大山
子;以孤独作茧,躺在茧里作蛹,仅以一种寄托作为出气孔的八大山 更不是
更不是 子。
子。
 子的心灵
子的心灵 处永远留给自己一个空白空间,它有着单纯和执着织成的栅栏,即便有心
处永远留给自己一个空白空间,它有着单纯和执着织成的栅栏,即便有心 让栅栏里鲜花璀璨,在
让栅栏里鲜花璀璨,在 子心中,远不如苍白依然。
子心中,远不如苍白依然。
小时候,国文老师跟我们说,寂寞就是孤独,孤独便是寂寞。有一天,当我擦亮惺忪的睡眼,开始读 生这部书时,下禁有些愕然寂寞太易,孤独太难!
生这部书时,下禁有些愕然寂寞太易,孤独太难!
为吾生须臾感叹,为似水流年留连忘返,随随便便心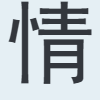 不佳,为花谢月缺伤感,在一个细雨霏霏的季节、在匆匆的月台送走匆匆的朋友、在飘雪的街
不佳,为花谢月缺伤感,在一个细雨霏霏的季节、在匆匆的月台送走匆匆的朋友、在飘雪的街 为一束凋零的玫瑰秉烛。
为一束凋零的玫瑰秉烛。
所以,寂寞太易。
国文老师的话倒像是极其朴素地描述了一种大彻大悟后的禅定,尽管并非也的初衷。
未参禅时,山是山,水是水;参禅时,山不是山,水不是水;禅悟时,山亦是山,水亦是水。
禅定是一种返璞归真的境界,是 类灵魂
类灵魂 处的梦呓。
处的梦呓。
禅定为形与意的统一,自然而然地充当了一切形的量度。
 子毕竟不是不染
子毕竟不是不染 间烟火的得道高僧,苛求不来禅定的洒脱:
间烟火的得道高僧,苛求不来禅定的洒脱: 子亦是凡夫俗子,要区别一种凡夫俗子与另一种凡夫俗子,寂寞就不能等同于孤独。
子亦是凡夫俗子,要区别一种凡夫俗子与另一种凡夫俗子,寂寞就不能等同于孤独。
寂寞足一抹忧郁的云,聚聚散散仍是一片一片,处于二维的概念体系里,于是我们很难意识到两种乃至多种寂寞感的 织。
织。
孤独则完全是一个三维概念,在陌生的群体里,你说没有 和你谈得来,你宁愿一个
和你谈得来,你宁愿一个 悄悄地缩在角落里。你的心此时被孤独
悄悄地缩在角落里。你的心此时被孤独
 包围了,被有容量的三维实体密封了,心囚于孤独的圈图里,你无力自拔,你无意自拔,这便是典型的八大山
包围了,被有容量的三维实体密封了,心囚于孤独的圈图里,你无力自拔,你无意自拔,这便是典型的八大山
本章未完,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。